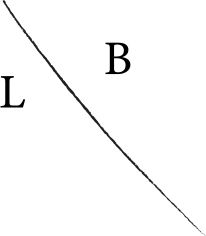远去的土地 远去的制陶术
馬永建 藝術史學者 廣東外語藝術職業學院副教授
影像可以記錄歷史,特別是記錄那些不但正從我們的視野中逐漸消失,甚至是將從我們的記憶中被抹去的歷史。《西南陶紀 -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制陶術》就是這樣一部具有歷史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的紀錄片。影片的拍攝者,陶藝家陸斌先生和譚紅宇女士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先後多次深入中國西南偏遠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展開深入的調查和資料搜集工作,並且用影像的方式向我們詳盡的展現了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原始制陶技術的面貌,同時也立體地勾勒出原始制陶技術在這一地區的地圖。
這部影片無論對於人類學、藝術史還是陶瓷工藝學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是現今國內乃至世界範圍內的第一部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及整理,全面記錄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原始制陶技術的遺存、發展形式和發展脈絡的紀錄片。
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制陶技術的出現無疑是原始社會生產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它改變了過去石器加工階段僅僅改變材料外觀的生產方式,而通過對陶土的塑形和火的使用,使泥土的化學性質發生了改變。制陶技術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一環,它的發展對於人類結束遷徙,轉入定居生活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時它在對火的使用上給後來青銅冶煉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不過,在普通人眼裏,與後來發展起來的瓷器所具有的高雅氣質不同,原始制陶始終具有一種平民化的特質,無論是原料採集、成型技術、燒制技術都比較簡陋,因而往往不被關注。一般的美術通史撰寫者也只是把它放在角落的位置上加以介紹,因而也很容易被普通讀者跳過這一頁。但實質上,正是因為其平民化特徵,原始陶器有著自身獨特的發展脈絡和頑強的生命力,並且與依賴土地為生的農業文明緊密相連,數千年來一直滿足著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的一些基本需求。在偏遠的地區,陶工們用土地無私饋贈的陶土製作各種生活器皿,演繹著亙古不變而又頑強不息的生存故事。
地處中國西南地區的雲南、貴州、西藏、海南等省份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由於這裏偏離中原且多為高原或海島地形,交通不便,在歷史上就形成了較為封閉的自然人文環境。時至今日,這裏的某些地區仍然沒有受到現代文明的浸染,還處於前工業文明階段。獨特的環境使得在歷史上就成型的生產生活方式在這裏被延續下來,也造就了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的“活的原始制陶術歷史文化博物館”的面貌——在這裏,原始制陶術並不是以遺址的形式被保存下來,而是以一種“活文化”的形態延續著自身的存在。各種制陶技術以口傳心授、代代相傳的形式被完整的保留下來,並且在今天的生活中仍然被採用。它們從成型方式上保留著從最原始的徒手捏制到輪制發展過程的各種形態,其大致可分為手制、模制、輪制三大類,而具體的方法則從捏塑成型、無輪盤築成型、泥片貼築成型、慢輪泥條盤築成型、泥條盤築拉坯成型、模具輔助成型、快輪拉坯成型到手動壓坯成型等方法都同時並存。而從燒成工藝來看,西南少數民族目前所使用的燒成工藝的種類幾乎涵蓋了人類發明了露天無窯堆燒技術到窯爐正式形成之間的整個過程。它們在歷史上是按照平地堆燒、坑燒、橫穴窯、豎穴窯、一次性泥殼窯、升焰式圓窯、倒焰式圓窯(饅頭窯)、龍窯、階梯窯的順序出現的,但是在此地區卻由於“歷史沉積”的緣故,平行的呈現出來。
這一文化現象的獨特價值在於人類各個階段按照線性歷史順序先後出現的制陶技術在同一個平面上展開,就如同熱帶地區的高山地帶從海平面到山頂蘊藏了各個不同溫度帶的植被一樣,有其特殊的豐富性和完整性,在世界範圍內來看都是不可多得的人類學、藝術史及陶瓷工藝學“活化石”般的文化資源。所以對這個地區所進行的深入調查,無疑對厘清制陶工藝發展脈絡及其具體形式變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影片的策劃兼導演著名陶藝家陸斌先生,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就開始關注並研究中國西南地區原始制陶技術的遺存情況,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資料。他與本片的合作者同樣也是陶藝家的譚紅宇,多次深入偏遠的村寨進行拍攝工作和跟蹤調查,積累了大量第一手資料。讓人感動的是,他們雖然不是人類學家,也不是專業的紀錄片拍攝者,但是作為陶藝家,在長期與泥巴接觸的過程中,陶土的那種單純的特質已經沁入了他們的氣質與內心世界——他們把自己定位為“陶工”。這反映出一種平凡樸實而又具有內在生命力的藝術理想。也正是這種理想,使得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他們與片中的那些生活在偏遠地區的陶工們可以心靈相通,產生內在的默契,並被原始制陶術獨特的精神氣質所征服,從而持之不懈的將這一工作深入下去。
同時,作為陶藝家的特殊身份和體驗使得他們恰如其分的運用鏡頭,捕捉到了陶器製作過程中那些不為常人所體會的細節表達。陶器的製作是一種純手工的行為,手與尚未成型的潮濕、柔軟陶土的那種特別的觸感和細微的動作所引起的形體變化只有陶器製作者才能真切的體會;而陶器燒制過程中那些相近形式的不同變體之間的差別也只有對其進行過深入研究的人才能準確分辨。這種用鏡頭書寫歷史的方式展現了一種比現場更加有感染力的能量,即通過對現場的深入挖掘和強化構造了一個更為清晰的現場。
記得我最初看到這部影片的那種震撼是難以言表的,這不僅僅是因為我藝術史學出身的緣故——它將那些停留在紙面上的抽象文字痕跡變成了一部活的、有著豐富細節和血肉的原始制陶術的歷史教科書和研究著作,更主要的是影片所展現出的那種與人的生存有關的原始潛能、力量、靈巧性及藝術感,這是在現代都市背景下很難看到的。而那些平凡的少數民族村民,憑藉著雙手和簡陋的工具,將一團團陶土變成了一個個具有實用功能的原始藝術品。透過鏡頭,我們看到濕潤的陶土如同變化萬千的精靈,通過製作者的手與心靈合二為一,達到了一種平凡質樸而又炫目的境界。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不僅僅是一部紀錄片,同時也是一件完美的藝術作品。它通過對原始制陶術的細節呈現,觸動了我們內心深處那些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已經漸行漸遠的情感,一種原本與我們的生命之根——自然、土地、泥土相互和諧的原始情感。
《西南陶紀 -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制陶術》的拍攝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即對這一地區的原始制陶術進行保護性的研究,並引起關注。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的腳步快速臨近,原始制陶技術賴以生存的社會、經濟、物質“生態鏈”正面臨被扭斷的危險。一方面,大量出現的工業品使原有的市場被破壞,大量陶工已經放棄了制陶手藝;另一方面,城市化的進程和旅遊發展加速了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掠奪性開發,使得越來越多的村民離開了土地。甚至在有些地區,制陶所需的黏土都成為了稀缺資源。影片中我們看到,在雲南西雙版納傣族的曼鬥寨裏,唯一做陶的婦女玉猛,為了延續世代相傳的制陶技藝,不得不在自己家裏囤積黏土,因為由於旅遊的過度開發,她已失去了土地…不難看出,這種無奈的舉動反映出了原始制陶術面臨的窘迫境地。
當然,我們好像真的沒有理由阻止這些地區融入現代文明,但是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不對原始制陶術進行深入研究並採取保護,其損失將是無法估量的。它是一筆不可再生資源,一旦失去,將無法重生。在這片幾乎一直處於現代文明視野之外的地區,還有很多散落的陶器製作形式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對它們的挖掘整理工作迫在眉睫。
如何對這些技術採取恰當的保護措施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畢竟,原始制陶術在來勢洶洶的現代工業文明跟前顯得是那麼孱弱無力。